1.
我在刺眼的阳光中醒来,翻了个身,眯着眼睛看了看床头的时钟,八点五十九分。
我想要多睡一会,重温刚才被中断的梦,梦里有一个面容模糊的姑娘与我坐在车库外面喝酒,但我却想不起我们谈了什么,我已彻底醒来,并因此万分沮丧,那个梦回不去了,就好像我失去了一段真实的时光那样。
我从床上爬起来,恍惚间总感觉今天有一件必须要做的事。
我住在北京东五环外一个很小的开间里,这里唯一的优势是采光良好。从冰箱里拿出凉的牛奶面包,我一边吃一边努力回想那件事到底是什么。
直到我看到墙角立着的吉他,我想起来了,和买家约定的日子就是今天。
这是一把马丁D28,美产,原木色,西提卡云杉单板,侧背板用的是东印度玫瑰木,这把吉他相当于我的全部身家,我当然很不舍,但没办法,活着更重要。
于是整整一天,我都在与我的吉他告别,内心像堵塞的高速公路,我只在偶尔回忆起那个支离破碎的梦,我想知道梦中的姑娘到底是谁,她会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人吗?
房间里响起枪花的经典名作Don’t Cry,那是我手机里预设的闹铃,我知道时间到了。
2.
交易地点定在后海。
从地铁出来后已经入夜,酒吧街的霓虹灯零星点亮,人们倾巢而出聚于此地,现在离这里的高峰期还有两三个小时。
走了一路,有点口渴,我来到一处报亭前,从冰柜里拿出一瓶矿泉水,递给老板两块钱零钱,靠着冰柜边喝边等。
买家迟到了,我不介意。
夜越来越深,一些酒吧的服务生开始出门揽客。每家驻唱歌手的歌声渐次响起,都是些我不太喜欢的大流行。
实在无聊,我点了根烟,再次想起梦中的姑娘。我随手抽出一份晚报,老板看了我一眼,没说话。翻到体育版,头条依然是北京奥运会的筹办工作,还有不到两个月就要开幕了,看起来一切顺利。第二版报道的是NBA总决赛的最终战果,波士顿凯尔特人队以4:2的总比分战胜了洛杉矶湖人队。
买家还是没到,现在我有点不耐烦了,拿出手机准备打给那个人,却看到大川在六个小时以前给我发过一条短信,上面写着:三缺一,你来不来?
3.
三缺一,这是我们的暗号,我没回复。
我拨通买家的电话,对面接起来,没等我说话就一个劲道歉,说不好意思堵车。我压着火,催他快点,再不来就不卖了。
我将翻完的报纸放回架子上,拎起琴箱,准备随便转转,迎面忽然撞过来一个人,我踉跄两步,手一松,琴箱跌落在地,发出令我心碎的声音。撞我的是一个穿黑色T恤的男人,T恤上印着电影《教父》的海报,我推了他一下,没用多大力,他却像保龄球似的晃了几下后摔倒在地,我意识到这人已经喝得烂醉,不想再纠缠,转头去检查我的吉他,还好只是琴箱略有破损,里面应该没事。
我骂了句傻逼,准备离开,那个醉鬼却突然来了精神,他晃悠着站起来,再一次扑向我,三两下后,我把他踹回去,惊觉周围已经围了两圈看热闹的人,醉鬼躺在地上,嘴里骂骂咧咧,我越听越气,但残存的理智提醒我必须得停手了,从小到大,我不知道因为冲动吃过多少亏,我站在围观人群中间,仿佛多年前登上的摇滚舞台,所有人的目光对着我,期待我做点让人兴奋的事情,我抬头看看夜色,再看看仍然试图爬起来的醉鬼,两个选项就像游戏机里转动的圆盘,不断在我的脑中切换着。
4.
从千山火车站出来的时候,我一眼就认出人群中的大川。
大川好像比以前胖了点,但说话声依然洪亮。他带着我来到停车场,将我的琴箱塞进了后备厢。上车以后,大川说,我还以为你不会回我的短信。
大川发动汽车,我问,你们怎么又想重组了?大川告诉我,千山开了一家酒吧,名字是我最喜欢的乐队,枪与玫瑰。说是酒吧,其实也是个livehouse,大川和几名原来的乐队成员一合计,竟再次燃起了少年时代的热血,如今各有安稳生活的大家,毅然决定重返舞台,纷纷将自家里那些落灰的设备搬进了大川家的车库,回到了多年前的排练时光,排着排着,就想到了当年的主音吉他手——也就是我,乐队里唯一一个离开千山去北京的人,那天在商讨之下,大川最后给我发了条短信:三缺一,来不来?
我来了。
大川问我这次是否打算留在千山,我说没想好,事实也的确如此,关于这次回来,更像是我的一次休整,在北京的发展不顺,没有得到什么也没有失去什么,只是我依然不知道自己究竟属于哪里,我决定在演出之前的这段时间里好好想一想。
到了车库,我看到了曾经的伙伴,鼓手佛爷,节奏吉他手宁子,大川是贝斯,一切就像昨天,仿佛我们从未分开。
一台橘子音箱上面放着主唱阿辉的照片,我看了一眼,立刻移开目光。大家默契地保持着沉默,我记得在阿辉葬礼的时候,我们所有人都穿着统一的黑色T恤出席,那是我们的约定,T恤上印着“骨音”两个字,是我们乐队的名字。
5.
虽然我带回来了这把马丁D28,但毕竟是一把箱琴,这些年在北京,为了维持生活,我卖了不少设备,其中就包括两把电吉他。不过大川早就给我解决了设备问题,车库里摆着一把Gibson与一把Fender,大川虽算不上富家子弟,但是比起我,他从未在生活上吃过苦。
排练还算顺利,那些多年前培养起的默契并未消失,我们先是重温了几首曾经的歌,又很快热火朝天地讨论起全新的原创,时间仿佛从未在我们身上流逝,人生的碎片拼接在一起,一如往常。
那个时候,关于留在千山还是北京的事,我心中的天平隐隐出现了倾斜。
不过排练也不是全然顺利,一个真实存在的问题始终盘踞在车库上空,只不过没人愿意提起。
一次休息的时候,我觉得这句话必须由我说出口,我们需要一个新的主唱,我先在心中说了一遍,接着看向大家,所有人似乎也都预感到了,停下来等着我,就在我开口之前,大川的手机响了。
大川走出车库接电话,几分钟后带着笑脸回来,说要出去一趟,没有人问他去哪,所有人只是沉默地坐在各自的乐器旁,平日喧嚣的车库里被按下了静音键,直到日落,大川回来,身后跟着一个姑娘。
大川指着姑娘对众人说,介绍一下,这是姚雨,我朋友,也是咱们的新主唱。
我们面面相觑,没有人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,大川走到我旁边说,姚雨跟你一样,也是从北京回来的。
6.
尽管如此,我还是没有跟姚雨说话,我虽然脾气不太好,但不得不承认,我却是一个容易害羞的人。姚雨梳着很乖的马尾辫,穿着土气的碎花裙,抓着手指拘谨地站在大川身后,与一切都格格不入。
姚雨扭扭捏捏,很小声地说自己刚回千山,还没回家呢,大川笑着送姚雨离开,并约定了第二天的排练时间。
第二天姚雨如约而至,她换了一身利落的T恤牛仔裤,但依然羞涩。
大川问姚雨准备得怎么样了,姚雨小心翼翼地拿出一张写满歌词的纸,动作谨慎得就像犯了什么错一样,我这才知道,大川已经提前将录好的DEMO给了姚雨,姚雨听了一晚,连夜写下歌词。大川提议走一遍试试,乐器奏响,姚雨将歌词放在谱架上,闭上了眼睛。
她声音响起的一刻,我知道我错了。
麦克风后面的姚雨,忽然变成了另外一个人,她被某个从天而降的神灵附体,飞升而上俯视着我们,掀起无名的漩涡,在这个满地线缆又脏又乱的车库里发出绚烂的光芒。
一曲结束,我已不知身在何处,却看到了演出当天的疯狂。
7.
演出前夜,大家都喝了不少酒。
大川搬来一台电视,我们一边喝酒一边看奥运会开幕式,开幕式还没结束,我们基本都醉了,胡话连篇,各说各的。我拎着酒瓶走出车库,坐在外面的水泥地上,刚才看开幕式的时候,我有些想念在北京的生活,尽管那段生活并不美好,此时却笼罩着一层平静的忧伤,我沮丧地明白,那段生活已经永远地离我而去了。
姚雨也走了出来,她坐在我旁边,虽然排练了很久,但我们一直没说过几句话,姚雨问我,你不冷吗?我摇了摇头。
八月的千山,夜晚微凉,可是当姚雨坐在我旁边的时候,我却不知道为何周身灼热。
姚雨似乎看透了我的心思,她问我,想北京了吧?我没说话。姚雨说,我也想了。她接着问,你在北京做什么?我说,没什么,混日子,你呢?
姚雨说,我在后海唱歌。
我不知道该怎么继续下去,酒精依然无法挽救面对姑娘时羞涩的我。姚雨倒不以为意,接着问我,你去过后海吗?
我说,去过,但不常去,也不喜欢,上次还出了点事。姚雨问,什么事?我说,当时我在那边约了个人卖琴,就是车库里那把马丁,结果人没等到,却跟一个醉鬼打了起来,不过也没什么事,那人连走路都打晃,根本伤不了我。
姚雨说,那还行。
我说,还行什么呀,他虽然打不过我,嘴上可不闲着,骂骂咧咧,当时好多人围观,我犹豫要不要再揍他一顿。姚雨问,你怎么选择的?
我放松了下来,笑着说,我没搂住火,还是下手了,围观的有人报了警,当天晚上我跟那醉鬼在地安门派出所蹲了半宿。
姚雨也跟着笑,她的笑声如夜晚的风铃,然后呢?
我说,然后也没什么,其实就在派出所里等那孙子醒酒,警察一看也没什么大事,劝我们私了,后来我们假模假样地互相道歉,跟拜堂似的给警察鞠俩躬就给放了。
姚雨笑得很开心,我看着她的侧脸入神,姚雨说这样也挺好的,至少你的吉他没卖。我说,没卖我在北京就没钱了,跑回来了。
姚雨说,那把吉他很好的,留着吧。我说,你挺懂啊。姚雨说,我也有把一模一样的马丁D28,不过后来摔坏了。
8.
大川晃晃悠悠出来,见我和姚雨坐在门口,舌头僵直地说,你俩拍电影呢——偷情男女?我问有这片儿吗,大川笑着说不知道。姚雨没理他,端着酒瓶仰脖喝了一口,大川接着说,你俩行,挺般配。
大川从我放在地上的烟盒里抽出一根,点着了回到车库里。这么一搅和,我和姚雨也有些尴尬,我们沉默着各自喝酒,一边喝一边努力寻找话题,半天,我问姚雨,怎么坏的?
姚雨说,什么?我说,你的吉他,怎么坏的?姚雨说,别提了,我在后海唱歌的时候,遇到了上台闹事的客人。
姚雨说着将她的右手伸过来,我一把接住,深情的凝视着她的双眼。姚雨说,想什么呢,让你看我手上的疤。我借着夜色仔细瞧了瞧,果然看到掌心的一条疤痕,与掌纹交错在一起,穿过了姚雨的命运线。姚雨说,就是那天被琴弦划的。我点点头,姚雨说,能松手了吗?
姚雨告诉我,那天早晨,她接到家里电话,又一次劝她放弃北京那份“不正经的工作”,姚雨有些动摇,但依然没有答应,可是到了晚上就发生了酒吧事件,摔坏一把吉他,留下一条疤痕,但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,最重要的是,那件事彻底击溃了她的心,那一刻,姚雨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思乡之情。
我问姚雨,那你这次回来,是不打算再回北京了?姚雨说,不回去了,你呢?你还回去吗?
此前我一直没想清楚这件事,但那一刻我的心里有了答案。我对姚雨说,大川这人吧,平时看着挺傻逼的,但是关键时刻说话还算靠谱。姚雨说,他说什么了?我借着酒劲说,他说咱俩挺般配,我也觉得,缘分这玩意真挺有意思……
姚雨打断我,别惦记了,她说,你没戏。
我问,为什么?
姚雨说,知道我家为什么一直劝我回来吗?因为早就给我找好了一个相亲对象,昨天已经见过了,年底结婚。
我抬头看着月色,没说话。姚雨笑着问我,怎么了,不高兴了?我说,刚见一面就结婚,你也太草率了吧。姚雨说,如果决定认命,就该彻底一点,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呢。我说什么问题,姚雨说,你还回北京吗?
我说,回。
我闷头喝酒,气氛凝重,姚雨没话找话地对我说,你们的歌写得挺好的,你最喜欢谁的音乐?我没好气地说,枪花。姚雨说,是吗,其实你别看我跟你们排摇滚,但我更喜欢流行,孙燕姿,你喜欢孙燕姿吗?我说,不喜欢。
我喜欢的流行歌手不多,但其实我喜欢孙燕姿。
姚雨说,你刚见我的时候是不是觉得我特乖?我没回应,姚雨接着说,其实我原来不这样,我在后海唱歌的时候从来不穿那种碎花裙,也不扎马尾辫,都是一身黑,披头散发。
一股莫名的悲伤从天而降,我不知这种感觉的来历,它令我无法阻挡,我对姚雨说,在你第一次跟我们合练的时候,我就知道那才是真实的你。
姚雨似乎也有些相同的感觉,夜色中她的眼睛里泛着一些晶莹的闪光,我渴望着她说些什么,但她却像个长辈一样揉了揉我的头发说,下辈子吧,下辈子早点认识我。
我将剩下的酒一饮而尽,姚雨起身回车库,我以为夜晚结束了,没想到几分钟后姚雨再次出来,手里拿着我的马丁D28,递给我说,给我伴一首孙燕姿的《遇见》吧,就当是纪念我们的相识。
我看着吉他,又看看她,接过琴站起来说,下辈子吧。
9.
那个夜晚后来发生了什么我已不记得,最后的印象是我回到车库里,继续灌自己酒,醒来时头痛欲裂。
今天晚上就要演出了,白天大家醒酒后各自回家整理,到了晚上我们相约在“枪与玫瑰”酒吧门口,我和姚雨对视了一下,什么都没说,各自与旁边的人说话。
来看演出的人不多,其中大多数还是大川找来的朋友,不过好处是大家都很捧场,我很快找到了久违的舞台感觉,我们唱了几首过去写的歌,到了中段,我换了把吉他,前奏响起,我们开始演出新歌。
新歌的反响不错,台下甚至出现了POGO的人群,我看着姚雨的背影,她动情地演唱,像个精灵。在我弹奏SOLO的时候,她回头看着我,解开头绳,长发飞流而下,在那一瞬间,我与自己和解了。我一边弹奏一边靠近她,我们在舞台上形成了默契的互动,我趴在姚雨耳旁大声说,答应我一件事。姚雨喊,什么事?我说,我走的时候,你要送我。姚雨抬头看着我,她说,我答应你。
忽然,什么东西贴着我的耳朵飞了过去,我回过头,看见一个啤酒瓶砸碎在鼓旁的监听音箱上,乐器声终止,现场一片混乱,我这才看清楚扔酒瓶的是台下一个胖子,看起来像是喝醉了,我的臭脾气上来,跳下舞台跟那人扭打在一起,那人虽然身材厚实,但明显不会打架,他下手绵软,几下较量后,我把他压在身下,左右开弓,这时候姚雨在台上用麦克风对我喊,住手!
我抬头看着姚雨的眼睛,她黑色的瞳孔中藏着深不见底的悲伤。她说,住手,就当是为了我。
我停下来,站起身,准备回到舞台上,那个胖子忽然对着台上喊道,你他妈不是说以后不出来卖唱了吗?
我疑惑地回头,看了看胖子,又看了看舞台上的姚雨,明白了。姚雨下来,站在我身边说,对不起。我说,这人就是你未婚夫?姚雨点点头。我说,他凭什么管你?姚雨说,你不懂,事情很复杂。我说,那你就解释给我听。姚雨没有回应,拉着胖子往外走,我在后面喊,还没演完呢,你去哪?姚雨对我摇了摇头,我知道一切都结束了,无论那是什么,都结束了。
一股无名怒火在我胸中燃烧,我十分确定的是,我的人生至少应该有一次控制住自己的冲动,我努力压抑,我发誓自己真的用尽了全力,直到我被某种力量驱使着回到舞台,随手抄起件东西便冲了回去,后来我才意识到我拿的是自己那把马丁吉他,我握着琴颈,高高举起,对着姚雨的未婚夫砸下去,琴箱发出闷响,一弦应声崩断,划过我的手心,穿过我的命运线,流出了血。
我被众人拉开,一步步推回舞台,在这个一切都已经搞砸的夜晚,我决定明天就回北京,这时候,我感到脑后一记撞击,我眼前一黑,失去了意识。
10.
我不知道自己究竟在医院里呆了多久,总之当我站在火车站的时候,天气已经彻底转凉。
乐队的三个人前来送我,我看着空荡荡的站前广场,问大川,车站的人怎么这么少?大川说,现在就是这样,没人应该在这个时候离开。
我继续扫视着站前广场,大川似乎看穿了我的心思说,姚雨应该不会来了。我点点头,其实我早就知道会这样,毕竟发生了那种事,我们彼此间最后一点脆弱的好感也随着我的吉他一起毁掉了。
我最后与他们告别,踏上了回北京的列车。
大川,宁子和佛爷目送火车远走,他们回到车里,谁都没有说话,大川发动汽车,几个人最后停在了一个小区门口,几分钟后,扎着马尾的姚雨走了过来,大川拉开车门,姚雨坐上副驾位。
姚雨看着他们,三个人都穿着相同的黑色衣服,上面印着我们乐队的名字——骨音。
姚雨说,送走了?大川说,送走了。
大川接着说,其实你应该去的,他一定也希望你去。姚雨摇摇头说,算了,事情都是因我而起,不好面对他的家人。大川说,你以后怎么打算?
姚雨说,活着。
11.
我在刺眼的阳光中醒来。
冰箱里有凉掉的面包和牛奶,我拿出来一边吃一边回忆做过的梦,梦中我和一个姑娘坐在车库门口喝酒,我不记得她的容貌,但却记得那种感觉,就像我真的经历过似的。
我还记得,那姑娘给我看她的掌心,掌心有一条伤疤,与掌纹交错在一起,我一定是把自己的经历投射到梦中了,因为我的掌心就有一条伤疤,我低头看着,却不记得这条疤痕是怎么弄的。
吃完牛奶面包,我恍惚觉得今天有一些事情要做,环顾四周,我看到角落里的吉他,马丁D28,这间房子里唯一值钱的东西,我想起来了,今天是我与买家约定的日子。
一整天,我都在与这把吉他道别,直到傍晚,我将它装进琴箱,出门上地铁,最后来到了后海酒吧街,买家还没到,我站在一个报刊亭前买了瓶水,一边等一边顺手拿起一份晚报,老板没管我,我随便扫了扫体育版,北京奥运会还有不到两个月就要开幕了,另一则新闻说,NBA总决赛落下帷幕,波士顿凯尔特人队以4:2的总比分战胜了洛杉矶湖人队。
正要走,迎面撞上来一个醉鬼,我手里的琴箱跌落,好在没有伤到里面的吉他,我看了看那个醉鬼,他的T恤上印着电影《教父》的海报,我怒火攻心,踹了他两脚,他躺在地上骂骂咧咧,此时旁边围满了人群,理智告诉我应该尽快离开,可我的双腿却依然不受控制地走上前去。
刚准备上脚,远处忽然传来一个声音——
住手,就当是为了我!
我心里一惊,停了下来,环顾四周人群,却找不到那个声音的来源,半天我意识到,这恐怕是我内心的声音在阻止我,地上的醉鬼还在挑衅,我低着头,像条野狗一样挤出人群。
继续向前走,此时的酒吧街已热闹非凡,到处都是拉客的服务生,但是却没有人上前找我,我猜可能是拎着吉他的缘故,让那些服务生以为我是驻唱歌手。
路过一家酒吧门口,我看到一片混乱,从窗户望进去,一个秃顶的中年男人正在声情并茂地说着什么,我听不见他的声音,脚步却不自觉地迈进酒吧,这时候我听见了中年人的声音,他说,你行行好,你要是不唱,我的生意就没法做了。
一个女人的声音说,吉他都坏了,你让我怎么唱?
我循着这个声音走去,找到了一个角度,那个女人身着一袭黑色,长发披肩,低着头,我看不清她的脸,但注意到她的手绑着绷带,隐隐有血渗出,我问旁边的一名顾客,怎么回事?顾客说,刚才有人喝醉了,上台闹事,把这姑娘的吉他砸坏了,琴弦伤到了手。我说,闹事的人呢,报警了吗?顾客说,还没来得及报警人就跑了,挺高一男的,穿了个《教父》的T恤。
台上的姑娘对旁边的中年人说,老板,不是我不想唱,现在我的吉他坏了,手也伤了,这还没有别的伴奏,你让我怎么唱?
我来北京多少年了?我自己也已经忘记。只记得每天都是一成不变的生活,曾经在千山的我,原以为来北京是为了冲破束缚,却没想到走入了更大的牢笼。我没有得到什么,也没有失去什么,像个旋转木马一样围着到不了的终点打转,直到今日,我依然不知道自己究竟属于哪里。
想到这些,我看到未来的人生卷动着巨大的黑色漩涡向我涌来,不由分说,不容争辩,在我对一切做出反应之前,我的双脚已经走到了那个姑娘的面前,我被命运驱使着,我问她,你要唱什么?
姑娘抬起头,我看清了她的脸,某种东西穿过了我乏善可陈的前半生,我们对视了一下,我从琴箱中拿出吉他说,我给你伴奏。
老板点头哈腰地过来递烟说,兄弟,你太仗义了,救场如救火。我接过烟,老板又转头看着姑娘说,姚雨,这行了吧。
我看着姑娘,姑娘看着我。
我又问了一遍,你想唱什么?
她说,孙燕姿的《遇见》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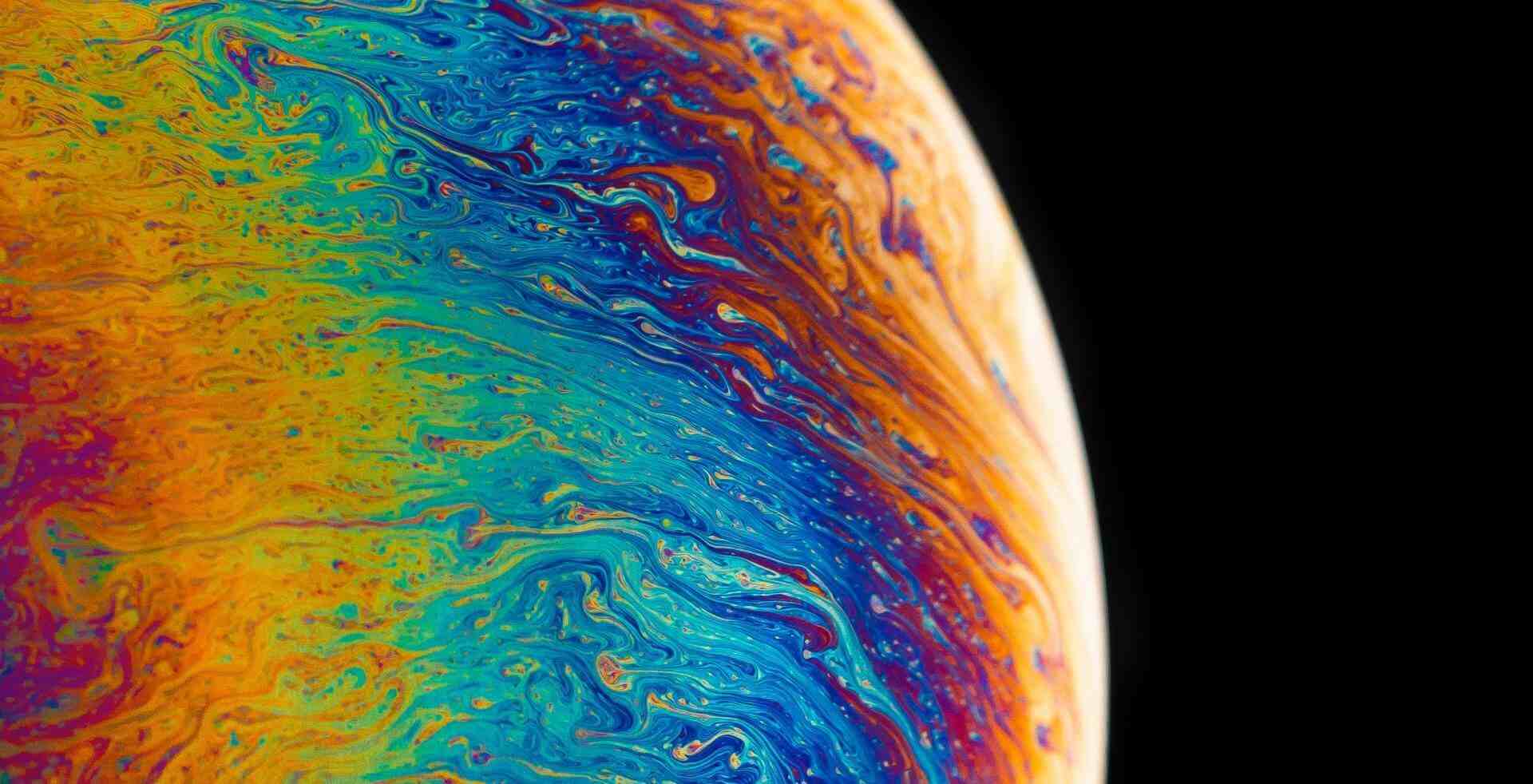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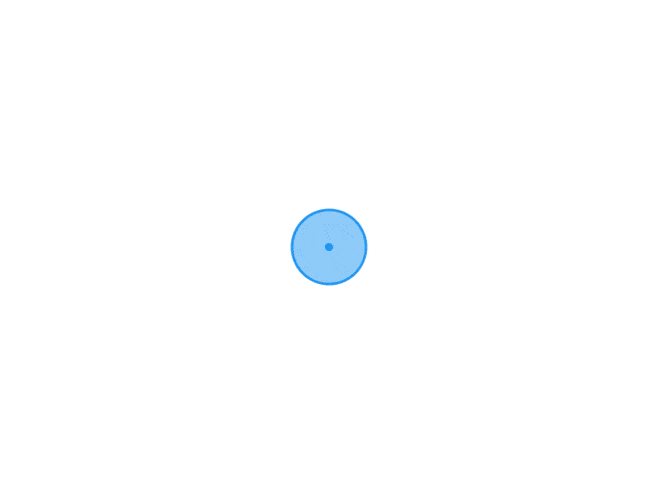
评论 (0)